行走豫州,读懂中国——“文科+X”中心河南研学活动
“文科+X”中心于2025年4月12日至16日组织师生共计22人前往河南省郑州、洛阳两地开展交流研学活动。团队拜访了河南博物院、龙门石窟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用脚步丈量华夏文明的主根系,在沉浸式体验中完成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


4月13日,同学们前往河南博物院参观一镜到底的九千年文明。河南博物院基本陈列“泱泱华夏 择中建都”展,由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东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七部分组成。该展以中原的建都历史为主线,以中原文明发展历史为纲,整合河南地区的文物优势,展示了华夏民族的文明发展轨迹,再现了中原文化的悠久与辉煌。
中心2023级博士生张恩瑞
在河南博物院中解构中原文明的基因密码,当我穿越河南博物院青铜色的大门,镇馆之宝如星辰列阵。贾湖骨笛七音孔的弧度里,藏着八千年前先民对音律的原始认知;莲鹤方壶上振翅欲飞的仙鹤,将春秋时期的铸造技艺定格成永恒的力学奇迹。在「泱泱华夏 择中建都」的常设展线里,二十二个王朝更迭的轨迹化作具象的青铜铭文、彩陶纹样与玉器形制。最触动我的,是展厅的「文物修复」——看着工作人员用显微镜拼接商代白陶的残片,突然意识到:我们凝视的每件文物,都是无数双手跨越时空的接力守护。这种将考古现场搬进展厅的巧思,让「文明传承」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为可触摸的技术伦理课。
中心2024级博士生林延廷:
从石器时代开始,以每个朝代的文明发展脉络陈列设馆,历史的厚重与古人的智慧展现的淋漓尽致。让我最为喜欢的则是青铜器展厅,它呈现出另一种时间性体验。站在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前,器物表面的饕餮纹饰仿佛在无声地言说。这些纹样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天命”观念的视觉化表达,是权力合法性的象征性建构,礼乐文明不仅是《论语》中的讲述,而是具体的呈现。我惊异于这些三千年前的器物如何通过物质性延续至今,成为连接古今的中介。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的一段历史,它们是河南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见证。

随后,研学团来到龙门石窟,对话石壁上的历史文明。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城南13公里的龙门山上,南北全长1公里,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就开始了龙门石窟的营造,历经10多个朝代陆续营造长达1400余年,现存2345座佛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中保留着大量的宗教、美术等方面的资料,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不仅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记忆,还承载世界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中心2024级博士生谷满仓
沿着伊河缓缓而行,两岸崖壁上密布着千年石刻佛像,气势恢宏,令人震撼。最壮观的是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神情庄严慈悲,石雕工艺精湛,充分展现了唐代艺术的高超水平。在龙门石窟研究院工作人员带领下,我们了解了石窟的历史背景及其佛教文化内涵,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的信仰和智慧对话。夕阳洒在佛像上,更增添了一份庄严与神秘。我们不禁感叹:那些凝固在岩壁上的佛像,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载体,更是历史变迁的实证。巨大的卢舍那大佛与艺术精湛的龛像,让我们深感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与责任。
中心2023级博士生刘小宣
龙门石窟,是整段旅程中最具精神重量的存在。傍晚时分的卢舍那大佛,在暮光与山影中逐渐显露情感的层次:初见悲悯,继而沉思。奉先寺的唐代力士造像,肌理之下藏着书法飞白的韵律,而某一处残破飘带上的匠人试刀痕迹,则将神圣拉回到人间:那些曾经的手、那些反复的尝试、那些几乎看不见的雕琢,都是文明真实发生过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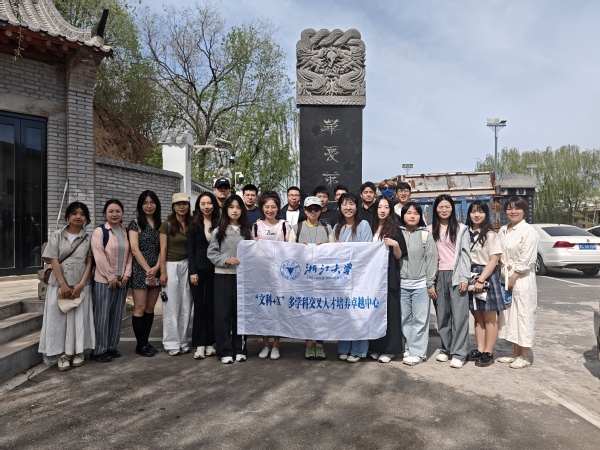
研学活动的收官站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距今约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二里头遗址内目前已经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了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揭开了古老“夏都”的神秘面纱。该遗址的开发和研究对探索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心2023级博士生刘小宣
二里头遗址,是一场从物质直抵精神的回溯。遗址区的探方剖面像一本打开的立体史书,不同颜色的夯土层将夏商更迭的秘密清晰标注。站在第三期文化层的灰坑旁,GPS定位显示这里正是《禹贡》中“豫州之域”的中心地带,脚下2米的深处,曾出土过一只陶豆的碎片,而它的存在,意味着这里可能曾进行过最早的粮食酿造实验。那些不起眼的残片,恰恰是中华文明从口腹之欲走向礼制之道的见证。
中心2024级博士生林延廷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现场提供了思考文明起源的独特视角。站在可能是夏朝都城的遗址上,考古学家徐宏的“最早中国”概念变得具体可感。那些夯土基址和青铜作坊遗迹,暗示着一个早期国家形态的诞生。二里头所代表的早期国家建构过程,正是这种文明突破的制度化表现。在遗址现场,时间不是均质的流逝,而是具有不同的“密度”,某些历史时刻承载着更为关键的文明转型意义。而在做遗址挖掘的工作人员也让我体会到了考古人员的热爱与坚守,与黄土为伴,保持耐心慢慢挖掘,这种耐心对于学术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心得节选】
中心2022级博士生张夏颖
我们既是历史的旁观者,也是文明长河的摆渡人。从二里头先民铸造的青铜器到龙门石窟工匠凿刻的佛像,从白马寺译经僧笔下的汉文佛经到牡丹园中嫁接培育的新蕊,中华文明正是在代代人的接续创造中生生不息。这一次研学既是触摸历史的朝圣,更是面向未来的启蒙。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当严谨探寻文明基因,敏感感知文化脉动,创新激活传统智慧。惟有如此,才能在河南这片土地上真正理解何谓“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
中心2023级博士生王璊璊
回顾本次活动,既是一次穿越千年的文化寻根,也是一场跨学科的学术洗礼。中原大地的每一处遗迹、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何以中国”的答案。在这个信息碎片化、技术媒介主导的时代,我们的学术研究往往停留于二手材料与文本分析中。而此次调研之行,则以一种“在场”方式提示我们:真实的生活、活态的文化、鲜活的个体,才是构成中国社会肌理的核心。
作为青年学者,我们当以更开放的视野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让传统在当代焕发新生。期待未来能将此行所得融入研究,为中华文明的当代表达与可持续传承贡献绵薄之力。
中心2023级博士生梁杰
此次河南郑州和洛阳的调研,让我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中原,这片古老的土地,孕育了中华文明,也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辉煌与衰落。博物院、遗址、石窟,这些历史的见证,文明的传承,让我们能够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与文明对话。读中国历史,不仅仅是了解过去,更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展望未来。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和源泉,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中心2024级博士生林延廷
通过此次河南之行,具身性的体验告诉我历史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客观过去,而是我们存在的构成性维度。文化遗迹之所以能打动我们,正是因为它们唤醒了我们存在中的历史性。每一次与文物的相遇都是“视域融合”的时刻,古代创造者的视域与当代观看者的视域在理解活动中交织。作为哲学研究者,我常常陷入概念思辨的自我指涉中,而这次文化考察让我重新认识到思想的肉身性。真正的理解不仅需要概念的清晰,还需要身体的在场与情感的投入。在郑州和洛阳的古老土地上,时间不再是抽象的参数,而成为可触摸、可感受的存在质地。
中心2024级博士生王晗
本次研学深刻展现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地位。从河南博物院里纵览各个朝代文明,到龙门石窟里见证佛教艺术的兴盛,再到二里头遗址上解读早期国家雏形,这些实地考察串联起了连绵的历史脉络。亲眼所见、亲身体验,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五千年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承与发展。研学过程中,大伙儿的讨论也越发热烈:关于历史文化的讲解激发了我们对古代社会结构、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兴趣。我们深刻认识到,博物馆与遗址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课堂,只有与真实文物和场景对话,才能更直观地理解历史。此次活动唤醒了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同学们纷纷表示,看到如此多承载国家记忆的文物和遗迹,倍感自豪,也更加明确了肩负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与责任。
这次跨省研学活动对个人专业学习和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实践证明,无论是文史专业还是理工背景的同学,都从跨学科交流中获益匪浅。历史与考古专业的同学通过实地观摩,加深了对文物背后历史背景的理解;理工科同学则体会到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三维建模等技术可以应用于考古发掘和遗址复原。这正体现了“文科+X”理念的价值:文科知识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视野,科技手段为人文研究赋予了新工具。例如,同学们讨论了用3D扫描技术重建石窟场景,用大数据分析文明传播等可能性。这次实践培养了我们的团队协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我们认识到创新思维和跨界合作的重要性。未来无论继续深造还是走向社会,我们都会把所学专业与对文化遗产的热爱结合起来,用专业知识和创新方式为传承历史文化贡献力量。
中心2024级学生王春璇
此次河南研学,让我从“触摸历史”到“理解当下”,重新定义了“何以中国”。白居易笔下“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坚韧,在河南的文化传承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无论历经多少风雨,中华文明始终如野草般生生不息,顽强生长。这种认知,让我内心的文化自信油然而生。正如古人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次也让我深刻体会到,只有将书本知识与实地体验相结合,才能真正读懂中国,传承文明。而我,也将带着这份收获与感悟,继续在文化探索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优选文章】
河南调研
中心2024级博士生 黄铭
2025 年 4月,我有幸跟随调研团队,踏上了河南这片底蕴深厚、孕育华夏文明的古老沃土。此次调研让我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一)中原文明核心载体的物质文化
调研首站河南博物馆,系统呈现了中原地区从史前到宋元时期的文化演进脉络。馆内陈列的贾湖骨笛、妇好鸮尊、莲鹤方壶等镇馆之宝,分别从音乐文明、青铜礼制、工艺美学等维度,勾勒出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核心载体的独特地位。
在而后的行程中,我们参观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群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原文化对外来宗教强大的吸纳与本土化改造能力。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的造像呈现出秀骨清像的独特风格,这一风格并非偶然形成,彼时鲜卑民族入主中原,带来了本民族独特的审美特质,他们崇尚简约、刚健的气质,同时,汉地儒家的人文精神早已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强调人的内在修养与外在仪态的和谐统一。二者相互交融,使得北魏造像面部清瘦、身形修长,线条简洁流畅,既有着鲜卑民族的质朴,又散发着儒家文化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到了唐代,卢舍那大佛以其丰腴典雅的形象令人瞩目,这一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昌盛,对外来文化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反映在艺术创作上,便是佛像造型饱满圆润,面部表情慈爱祥和,彰显出大唐盛世自信、包容、大气的文化心态。
(二)二里头遗址与早期国家形态
踏入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映入眼帘的是层层叠压的文化地层,令人深感震撼。从专业的考古学视角来看,不同颜色与质地的土层,恰似历史的年轮,每一层均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堆积。考古学家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和打破关系,得以构建遗址的相对年代序列。于宫殿区遗址中,各土层出土的陶器残片、兽骨、石器等遗物,犹如散佚的历史密码,经过类型学排比,逐渐拼凑出夏代晚期都城的生活景象。遗址现场关于功能区划分的演示,揭示了早期国家的社会组织结构。研究人员根据土堆的高度、走向及分布规律,判断出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区、墓葬区和居民区的空间布局。
田野工作场景中,考古工作者以毫米为精度清理地层的实践,彰显了考古学作为实证科学的严谨性。每件文物的出土语境(方位、层位、共存关系)均需精准记录,这些基础数据构成后续类型学研究与社会复原的起点。从十年前盗墓猖獗导致的文物破坏,到如今卫星监测、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助力文物保护的转变,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考古工作者不仅是历史的发掘者,更是文明的守护者。
(三)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思考
1. 考古发掘与民生保障的良性互动
我们在遗址保护区内看到的农田景观,是阶段性发掘完成后,研究人员将整理后的土地出租给当地村民耕种,既保障了农民的传统生计,又通过农业活动对遗址形成自然保护 —— 农作物根系的固土作用避免了水土流失,定期的田间管理防止了人为破坏。这种 发掘 - 保护 - 利用 - 反哺的模式,为大型遗址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当未来需要进一步考古工作时,可通过合理的补偿机制收回土地,实现学术目标与社会利益的动态平衡。2. 考古学术成果的社会化路径
作为 “最早的中国” 重要实证,二里头遗址的保护已超越文物本体层面,成为中华文明基因传承的文化工程。当前推进的遗址公园规划、数字化成果传播、考古体验项目,正将专业研究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资源:现场科普展板、博物馆互动装置、青少年考古夏令营等多元形式,有效消解了学术壁垒,使考古学从 “象牙塔” 走向公众生活。
此次调研以物质遗存为切入点,串联起文明起源、文化交融、遗产保护等核心议题。从博物馆的器物叙事到田野考古的地层解读,从专业研究的实证逻辑到社会参与的价值转化,河南之行深化了我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学理认知。
河南心得:在中原大地中追寻文明脉络与时代回响
中心2024级博士生 王奔
此次河南的调研之行,不仅是实地的田野调查,更是一次沉浸式的文化洗礼。我们从杭州启程,经郑州、洛阳,步入黄河文明的源头,追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与魂。在短短几日的行程中,我们走进河南博物院、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探访龙门石窟,深入二里头遗址,跨越数千年文明的厚重,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获得了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一、在数智时代读懂“河南”的意义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二里头遗址,再到盛唐时期的洛阳文化,河南见证了无数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此次调研活动,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自信”如何在地方治理与社会发展中具体落地,另一方面,也能促进我们将专业所学与现实场景相结合,探索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二、调研之行的河南观察
(一)走进博物院:感受中原文明的起笔
此次调研活动我们参观了河南博物院和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中收藏着数量庞大、种类丰富的文物,从原始社会的陶器、青铜时代的礼器,到汉唐时期的文物精品,串联起中原文化演进的主脉。在观展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文明累积的力量”。如贾湖骨笛、妇好鸮尊等标志性文物,不仅展现了古人精湛的工艺,也传递出古代社会的审美、信仰与礼制体系。尤其是博物院展览所采用的现代化展示技术,也体现出文化传播方式的现代转型,也为我们从事传播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观察样本。
(二)龙门石窟:与“硬”历史的时空对话
调研第二天参观龙门石窟,这座世界文化遗产以其数量庞大的佛像与雕刻艺术震撼人心。在千年石窟的背后,承载的是怎样一套关于国家、宗教与文化传播的机制?龙门石窟不仅是佛教东传的历史见证,也是古代文化全球化的实物证据。而在今天,它成为地方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支点。
(三)二里头遗址:寻找“夏”的踪影与国家的雏形
调研的重头戏之一是二里头遗址,它被广泛认为是夏文化的重要代表。这不仅是一处考古遗址,更是国家起源的重要线索。通过考古老师的介绍与现场观摩,我看到了古代的第一条十字路口,意识到国家治理的雏形、城市结构的初具、青铜礼器的分化,均在这里萌芽。二里头遗址展示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演进过程。在传播学的角度看,它也是古代信息制度的源头,比如祭祀制度中所蕴含的“仪式”,青铜器上铭文的“符号”,乃至宫城结构中的“空间传播”。这些都为我们探讨国家叙事与文化根源提供了珍贵的田野证据。
三、反思与启示:对传播路径与文化表达的思考
在本次调研活动中,我格外关注地方如何通过“讲好自己的故事”来实现文化影响力的延伸,观察其他学科如何理解自身的传播以及传播行为的实践。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译。无论是河南博物院的数字导览系统,还是龙门石窟的网络宣传,都体现出地方在积极拥抱新媒体,提升传播效率与用户体验。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实现“文化IP化”“传播场景化”等关键变革。唯有如此,地方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被更多人所理解。
河南调研之旅虽然短暂,却让我们在现实与历史交织的语境中,触摸到了文明的肌理与温度。中原文明具有极强的延续性,从仰韶文化到汉唐盛世、再到当代的地方文化建设,其文化符号、制度逻辑和传播机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新时代的传播内容与表达形式。传播方式的趋于多元化与技术融合,地方话语与全球叙事之间的融合正在成为主流趋势。作为青年学子,我们应当主动拥抱跨媒介表达、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成为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国家、历史与未来之间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