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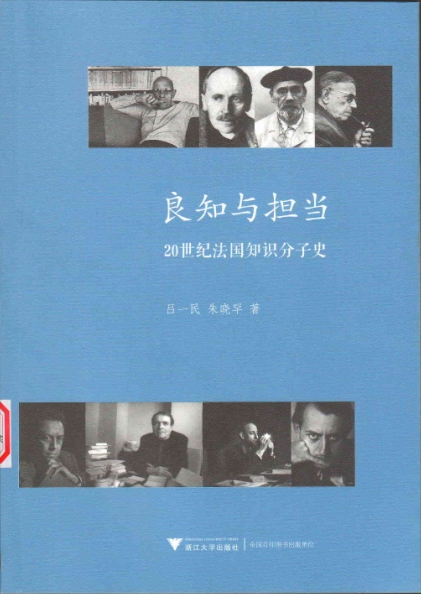
坚守良知、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作为社会冷静的旁观者和批判者,还是作为社会热情的“介入”者和规划者,对其所在社会的良性发展可谓不可或缺。
虽然“知识分子”的界定至今仍歧义纷呈,但世界各国的人们在谈到知识分子时,脑海里往往会浮现出法国知识界一些著名人士的形象: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愤然宣布“我控诉!”的左拉;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时代的良心”的萨特;积极充当法国监狱改革运动等诸多社会运动先锋的福柯;不时以反“全球化”的斗士或自由资本主义的狙击手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布尔迪厄······ 显然,上述人士已被世人奉为知识分子的楷模。事实上,法国知识分子似乎有太多的理由被世界各国的同道所羡慕。在他们看来,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20世纪、尤其是战后“辉煌的三十年”的法国知识分子那么高的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享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起着如此之大的社会作用,以至于他们的言行几乎时时刻刻都成为法国传媒(有不少时候甚至是国际传媒)关注的焦点。
有鉴于此,本书系统地梳理了法国知识分子从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所走过的历程,对他们在法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变迁进行了探讨。全书30余万字,分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时期、战争与危机的年代、“辉煌的三十年”和“终结”的时期四大阶段展开论述。主要观点有:
一、德雷福斯事件不仅为法文“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一词的“诞生”提供了语境,而且,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在充当“社会的良心”,“介入”社会生活中所采取的手段及表现出来的特点,大多可在这一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身上找到先例;更有甚者,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的一些重要现象,如知识分子内部的“两极化”(bipolarisation)、普遍主义(le universalisme一译“普世主义”)或世界主义(le cosmopolitisme)与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持久对立、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与反理智主义(l’anti-intellectualisme,一译“反智主义”)之间的斗争以及20世纪法国知识界突出的“左倾化”特征等,均发端于此期。
二、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是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辉煌的三十年”。随着二战的结束,法国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可以用萨特的名字命名的时代。在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中,“自由选择”是其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自由选择”无疑包含着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而积极入世,对于二十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社会的“介入”。萨特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始终无愧为是这种“介入”的最理想的化身。他在战争后期与战后初期的种种表现,更是在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方面为战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作出了表率。而从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维度来看,“萨特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亦可视为战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辉煌的三十年” 的同义词。
三、1968年5月风暴是第五共和国潜在危机的总爆发。在这场表面看突如其来的事件中,法国的各派知识分子照例做出了自己的反应。由此,曾一度对政治有所厌倦的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呈现出重新政治化的趋势。更有甚者,一度失势的存在主义竟在五月风暴中重新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而结构主义则在取代存在主义方面受到了重创。值得注意的是,5月风暴过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队伍明显地发生分化。一些人继续坚持激进的革命态度,甚至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戴高乐派政权;另一些人则在对5月风暴的结果失望之余,认为马克思主义“欺骗”了他们,因此,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偶像从阿尔杜塞、毛泽东和马克思转向拉康、福柯和索尔仁尼琴,从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转向公开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新哲学家”就是后一类人的典型代表。
四、从80年代初开始,法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舞台上显得非常的低沉。知识分子的“沉默”,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一时间,媒体在谈到知识分子时开始频频使用“危机”、“衰落”、“终结”等词语来形容法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对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角色定位与作用重新进行审视。在这一过程中,利奥塔发表了《知识分子的坟墓》一文,耸人听闻地提出,不应该再有“知识分子”了。显然,他让自己扮演了“知识分子的掘墓人”的角色。诚然,利奥塔的结论很难让我们全盘接受,但它至少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20世纪晚期的法国知识分子在调适自己的社会角色时遇到了不少难题,存在着许多困惑。其中,他们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去应对自己的“认同危机”,或曰“身份危机”。
五、在20世纪晚期,尤其是在苏东国家发生剧变之后,在法国知识界,卢梭-萨特一派的激进思想日趋衰落,而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阿隆的传统自由派思想却逐渐占据上风;与之同时,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科技知识分子的中心化趋势加剧,知识体制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束缚愈益严重,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知识分子“非政治化”现象进一步突出,批判性明显减弱,知识分子中左-右之间的分野日渐模糊;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不少知识分子更加热衷于同媒体打交道,并因此不惜屈从于市场法则,弱化自己的独立性······
如果说,上述特点可以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终结”的注脚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发生在“世纪末”的下列事例中看到,在法国知识界内部,以左拉、萨特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余韵尚存,法国当代知识分子仍保持着一份公共的关怀:集体要求法国政府用外交或其他手段对发生在波黑或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进行干涉;发起“无国界医生”、“世界医生”运动;隆重纪念左拉的《我控诉!》发表100周年……。而书中以“为征收托宾税以援助公民而斗争”(ATTAC)这一组织为切入点重点加以考察的法国知识分子在反全球化过程中的表现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证。
本著作的主要研究思路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以知识分子和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为主线,对德雷福斯事件爆发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在法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些作用演变的趋势或规律进行剖析;在研究过程中,力图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中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充分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一个世纪为时段,从整体上对某个欧美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展开综合性的研究,这在国内尚属首创。与国外学者的同类研究相比,本书的研究内容有所扩展,时间下限也有所延伸,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本书可以丰富我国20世纪世界史、西方社会文化史和法国史的研究内容,对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或领域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